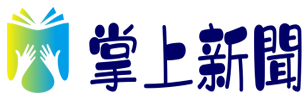2月23日,電影《生息之地》在柏林電影節上獲得銀熊獎的消息傳回。銀熊獎,就是最佳導演獎,獎勵導演的。柏林電影節認爲,《生息之地》的導演霍猛拍得好。基於影片故事,我聊一些個人看法。

爲什么是最佳導演獎,不是最佳編劇或者最佳影片。
最佳導演獎,其實就是獎勵導演的,認定這部電影拍得好。同時,也可以反向推導,《生息之地》的劇本,離最佳,還有距離,整部影片,離最佳影片,也有距離。爲什么是拍得好,而不是劇本或者成片本身更好呢?因爲《生息之地》講的,其實是一個中國影迷熟悉,歐洲影迷也相對熟悉的內容。
柏林電影節給《生息之地》最佳,看重的是,這部電影具備中國民族祕史價值。早前,嚴肅文學作品,尤其是長篇小說作品,承載“民族祕史”的任務。在歐洲不少的電影節上,也認爲,電影應該承載這個“民族祕史”的任務。《生息之地》恰好承載了這個任務,但故事內容方面,承載的一般,那就獎勵導演拍得好,算了。

“民族祕史”是個啥?
宏大的,天天新聞上播報的,能夠真的被記載到歷史史冊當中的,那些,都不算民族祕史。比如說,咱們好多年代劇,一要呈現具體年代了,就是鐵榔頭拿世界冠軍了,香港回歸了,哪個宇宙飛船上天了等等。這些,都不算民族祕史,只算時代標籤和符號。民族祕史,講的是新聞上沒有播報的那些相對私密的內容。
《生息之地》講的,就是相對私密的內容。上世紀九十年代初,在河南的一個鄉村,這一年當中,出了幾個葬禮,和一個婚禮,出了交公糧的事情,出了計劃生育的事情,出了生存不容易的事情等等。這些事兒,是生命個體的,是一個鄉村的。但是,同時,它也是整體的,是一種最具普遍特徵的事兒。但是,這些事兒,不被新聞和歷史記錄。
記錄它們的,曾經是小說,現在,是電影。

電影,是落後於小說的。
《生息之地》這部電影,要是國內能上映,估計國內影迷看完了之後,會覺得,和自己曾經的鄉村生活相通。沒有農村生活經驗的影迷,可能夠不到這部電影的內容情感。這部電影,國內現在能看到預告片了,是農田裏邊,幾個人相遇,然後开始披麻戴孝,並且开啓吊孝表演。這是白描,不是導演設計的,是曾經的農村生活,就是如此。
在這一題材內容上,電影是嚴重落後於小說的。中國文學當中,莫言、劉震雲、閻連科等一批老前輩們的內容,從上世紀初,一直寫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。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的農村故事,老前輩們夠不着了。這些老前輩們都進城了。雖然這些老前輩後來有一些,又重新回到鄉下,但他們是以作家的身份回歸的,看到的生活,已經蒙上一層“塑料布”了。
老前輩們的衣鉢,也有一些作家繼承,繼續寫,從上世紀九十年代,寫到新千年,寫到第一個十年,和第二個十年。有些青年作家,寫得也非常好,真實,是真正的農村人和農村光景。我就不打廣告了。
咱們中國電影,就比小說要落後很多。中國電影導演,好多都不熟悉農村生活。中國導演,好多都特別有錢了,他們的認知當中,开寶馬都算窮人。像《生息之地》的導演霍猛,他是84年生人,河南人。他在《生息之地》當中呈現的農村,其實就是他不到十歲的時候,看到的農村場景。
從看到這個農村,到用電影的方式講出來,霍猛用了三十多年。中國電影,也落後了中國小說,三十年。

無論電影,還是小說,都有一個當下性的價值所在。
我們站在2025年,講1991年農村的“生之多艱”,當然也有價值。比如說,歷史價值,尤其是文學的、影像學的歷史價值,民族祕史價值等等。但是,這個價值,總是讓人覺得,不如講當下的故事,更有價值。比如說,站在2010年前後的郝傑,用《光棍兒》講2000年前後的張家口農村故事,就顯得更具備當年的當下價值。站在2025年的霍猛,講1991年的河南農村故事,就顯得有點遠了。
所以,中國電影和中國文學,還是要多謀求講當下故事。比如說,我是文學創作者,那我就講一個2025年農民工如何進城打工的故事,這個故事,肯定和十幾年前或者幾十年前的農民工進城打工,不一樣了。這是體現本事的。因爲以往的文本當中,沒有範例,我只能自己採風,自己挖掘,自己創作。
霍猛這個,不太體現本事兒。因爲他講的那個故事,其實好多人都講過了,他當然有自己的真情實感,但更多的,是站在前人肩膀上“創意寫作”罷了。老外畢竟讀中國文學少,一見《生息之地》這么白描,當民族祕史了,自然給了大獎。中國電影唬老外,確實可以把他們唬得一愣一愣的。但《生息之地》,不太容易把真讀書的自己人唬住。
當然,還有另一句話,做最後的結尾——也甭嘲笑霍猛,好多導演,連白描的能力都沒有。(文/馬慶雲)
鄭重聲明: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,轉載文章僅為傳播信息之目的,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,如有侵權行為,請第一時間聯絡我們修改或刪除,多謝。
標題:柏林電影節銀熊獎《生息之地》,河南鄉村白描,歐洲人當歷史看
地址:https://www.newsipad.com/article/189276.html